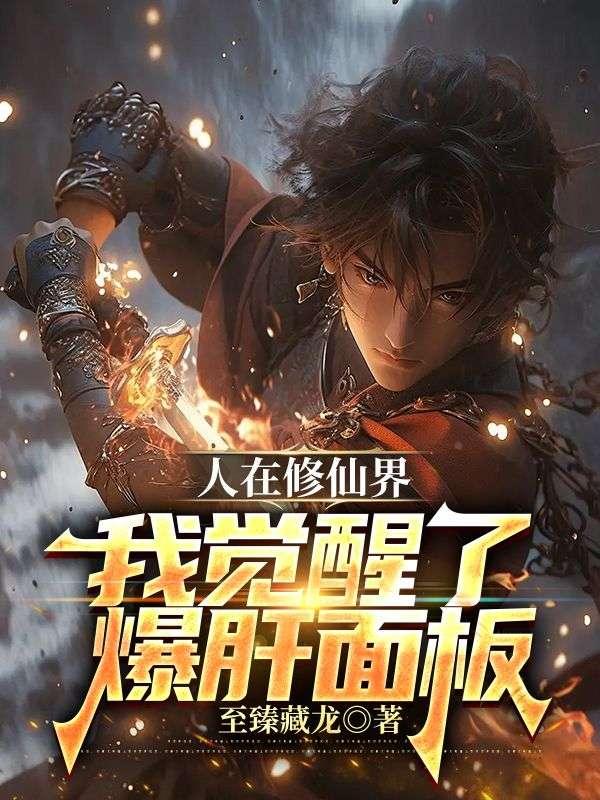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拏云 > 赴会(第1页)
赴会(第1页)
“老夫凌畅,没想到,原来梦枯荣,孟医士是这样一位年轻俊俏的娘子,失敬失敬!”
凌家家主在正厅,笑脸相迎。
凌家这一任的家主名唤凌畅,他倒是金盆洗手,从未做过梁上君子,才好继承了偌大的家业。
可是家里的小辈不老实的多得很,比如重病不愈、昏迷不醒的那一位凌纷若郎君,可是黑白两道通吃的盗贼头目。他有个江湖诨号叫“盗金田”,据说他偷来的宝物能铺满凌府山下的稻田,也有传说,他偷走了东番皇族皇陵一整片埋金田中的宝贝。
也因此,凌纷容在江湖上的名声不好,声名鹊起的好人家医士不愿救这个无德之人,寻常的医士又治不来他的病,拖了七日,人都快拖死了。
孟华龄倒不在乎这些虚名,“梦枯荣”在江湖上也没有甚么好名声,要怪就怪孟魁元年轻气盛之时,也做下了过伤天害理之事,以至于他行善积德,不为“枯”,只兴“荣”了这许多年,还是没翻转过江湖中人对他的印象。
但是医术了得是做不得假的。
凌畅套近乎道:“老夫在孟医士这个年纪,就听闻过孟医士的大名了,您这就叫,子承父业?”
孟华龄对于凌畅在她面前摆长辈的谱不置可否,她摊开了针囊,将梦枯荣的一手金针给凌畅验看,说道:“因为我十成十继承了家父的衣钵,所以也继承了家父的名号,梦枯荣正是在下。凌家主,无需什么客套,我先问一句,若是医好了令郎的病,凌家主说有赠礼一件,是也不是?”
凌畅惊讶于孟华龄这毫不拖泥带水的作风,同时也对此十分欣赏,他拱手答道:“不错,孟医士但说无妨,若是能治好小儿的病,莫说一件,就是三件、五件,凌家也会吝啬。”
他也不愿在叙话上耽误许多功夫,毕竟来的医士那是越多越好。
“贵府可有两味药草,鸳首灵芝,定系蚕丛月轮花?”
凌畅一愣,这两个名字对他来说有些陌生,他唤来管家,叫拿府库的记录簿来,转头对孟华龄笑道:“孟医士,不若先去看看小儿的病?这两味药听着耳熟,只是不知府库中的存量。”他的目光又投向了孟华龄身后跟随的孟松年与贺振云二人。
“此乃舍弟和——”孟华龄在唇齿间挑选了一个名号,只片刻就接上了话,“打下手的药童。”
没错,身高八尺的药童。
至于凌畅将二人哪个当做药童,哪个当做孟家小郎,孟华龄一时间没意识到可能会出现这般的纰漏。
凌畅右手平伸而出,指引道:“三位,请——”
正此时,门外又抢进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医士,他肩上背着个大药箱,留着两撇小胡须,下颌续着一缕山羊胡,风尘仆仆地抢将进来。凌家仆人跟在后面也跑了几步:“诶呀,莫医士,您老慢些走!”
“啊呀,莫老,是您大驾光临!”凌畅收住了脚,和这位莫医士寒暄了几句。
原来,此人姓莫,名望冲,在江湖中也有些名气,中年时就自称“三才老儿”,是个半路出家又还俗的道士。
莫望冲哈哈一笑:“凌家主等等小老儿,等等——这位娘子又是何人?”
“在下梦枯荣。”孟华龄淡淡道。
凌畅将二人引荐一番,那莫望冲眉毛鼻子皱成一团,“小娃娃,你爹是你爹,你是你,可别将他一世英名都毁坏了去,你回家可怎么见人啊?”
孟华龄冷淡地觑了他一眼,“老先生,口说无据,须得见真章。”
“医士们先同我前去吧。”凌畅打了个哈哈,引着四人步出前堂,穿过一个大花园子,行到内宅。
凌纷若这间院子堪称一座金库。
孟华龄也吃了一惊。
凌家的正堂是简约大气的布置,挂画装饰也是梅兰竹菊四君子,清雅别致。
可这凌纷若郎君的院落里,诶呀呀,真不得了,他定是从富贵乡里滚出来的,房内白日里灯火通明,不用油灯,而是点起了一排儿臂粗的红烛。床前榻边放置了许多个冰盆,被蜡烛一烤,消暑的功用也降低了不少。
房中的帷幔、锦缎一应采用樱桃红色织锦,上绣着团团盛开的各色繁花,那可真叫人眼花缭乱。
窗纱却是绿茵茵的软烟罗,是浅浅淡淡,低饱和的橄榄绿色。
正房面对面排着两张七八尺高的博古架,孟华龄扫了一眼,入目一对金银平脱鸳鸯花鸟纹铜镜,下面一层是一把螺钿紫檀琥珀漆艺琵琶横放着,似乎破坏了博古架宝器的原有的格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