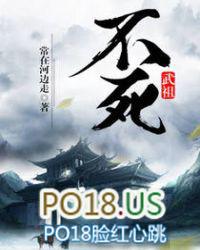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高岭之花他追悔莫及 > 第 121 章VIP(第3页)
第 121 章VIP(第3页)
他来了之后,才知道距离京城千里的西域是这个模样,仿佛已经脱离了大雍的国境。
若是此战输了,胡人想要东进就更容易了,打到京城都是可行的。
有从京城进来的年轻小将义愤填膺,主动请战先行去冲杀一波。司徒征摆手,拒绝。
见他失落,司徒征道:“怒可以复喜,愠可以复悦;亡国不可以复存,死者不可以复生。*战事前谨慎些。”
几人又围着阵型图,仔细商议了一番。司徒征定了常年驻守西域的老将领左军,适才主动请缨的年轻人领右军,他自己则坐镇中军。
残阳如血,荒地上两军对垒。战事吃紧,司徒征率部赶路匆忙,他知道皇帝还会派五万援军来。但眼下不得不打,不得不赢。只有挺过去眼前的大军来犯,才能等到援军。敌方声称十万大军,去除伙夫民夫和老弱病残,真正能打的不到六万。但司徒征清楚己方能打的不过八千人。
战鼓隆隆,两方交战,厮杀声震天。敌方等待已久,加上因为急于立功而行列混乱,但人数众多,依旧是碾压之势。见状,司徒征亲率麾下五十骑,横向击之。他冲在最前面,冲入又杀出,如此反复多次,血染铠甲,整个人在暮色下,如浴血修罗,令人望之生畏。
这铁骑分割战术,终于将敌军一分为二,愈发混乱,战力大大减退。左军右军呈包围之势,两相夹击,开始围攻起失去将领指挥而逃窜的异族敌军。
天渐渐黑了,司徒征浑身是血,有别人的,更多是他自己的。身上大大小小都是伤口,还有箭贯穿肩膀,夜幕下,他脱力从马上摔下,意识模糊里听见了雍军追击虏敌的叫嚷声。
他闭上了眼睛。
不知过了多久,乌沉沉的夜里,有手执火把的将士来打扫战场,救治还活着的人。韩岱等司徒征的下属都大声呼喊着他的名字,虽是护卫,但战场上绝对没有贴身保护的说法。韩岱自己也受了刀伤,焦急地寻找司徒征的身影。
终于,韩岱见到了熟悉的身影。几人举着火把上前一看,司徒征身下全是血,面上苍白,呼吸微弱。
“郎君!”
几人小心翼翼地将司徒征抬起到平板车上,运回营帐。军医诊治了一夜,出来时重重叹了一口气。
此战大获全胜,杀敌一万,俘虏三万,就连捡胡人逃跑时丢下的盔甲都捡了个大丰收。可偏偏功劳最大的主帅,性命垂危。
这些消息都已经八百里加急送去京城。韩岱,青筠等人都是日夜守在司徒征的帐内,三日后,司徒征睁开了眼睛。
他人虚弱,语气却是平静,让下属汇报。
听完雍军彻底大胜,援军也已经快到了,不论是在此耗着还是主动出击都是雍军成了有利的一方,他微笑了一下,重新合上眼睛。
“郎君!”
几日后,京城援军赶到,他们路上遇上了皇帝的信使,命司徒征回京救治。一行人平缓地上了路,司徒征开始反复发热,难得有清醒的时候。
这夜,司徒征醒了,平静地听韩岱吞吞吐吐说了众多医士的诊断。
他很难再站起来了。不光如此,伤势太重,即使回到京城,什么灵丹妙药吃下去,恐怕也只是强行续命,难以撑过今年。
“郎君,陆神医一定有办法的。”韩岱恳切道。但他知道这些话说出来不过徒劳,连只给皇帝看病的御医都已经诊治过了。
司徒征动了一下手指,吩咐道:“我说,你写下来,拿我的印信来。一回京立即去做。”
京城,定远侯府。
定远侯夫妇看着苍白如纸的儿子,俱是错愕无比。京城里所有名医,包括陆谨都进去了,一个个出来时都是面如土色,唉声叹气。
房夫人怔怔道:“我去将永穆县主接回来,我这就去。”
“夫人!”韩岱叫住了她,将司徒征途中口述的信拿给她看,“您先看看这个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