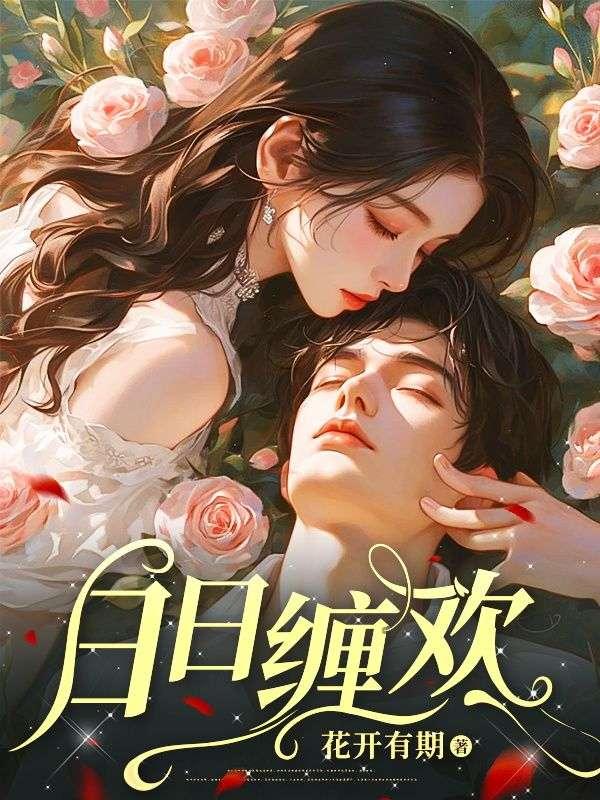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彼岸花落时 > 第12章 封闭的护理室 回忆(第4页)
第12章 封闭的护理室 回忆(第4页)
大腿肌肉因紧张而微微绷起,贴着制服内侧的棉质底裤有些贴肤,隐约勾勒出她身体未曾暴露却依然存在的女性轮廓。
她闭紧嘴唇,肩胛骨紧绷,像一只被钉在展示板上的昆虫,动不得,喊不出。
那只手终于探入她的制服下摆——不是用力,而是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轻巧,像一根潮湿的羽毛在试探,顺着她腹部下缘一寸一寸抚过,动作并不快,但每一秒都拉得极长,几乎能听见空气因皮肤与布料的摩擦而起的轻响。
她的呼吸开始断续,双唇颤动,喉头像被卡住,发出一点点气音。
她的身体没有发出尖叫,也没有挣扎,那是本能在保护核心器官——收缩、封闭、冻结。
她的背被汗水打湿,制服后背紧贴金属床栏,冷得像冬天的湖面。
她能感受到自己的乳房因呼吸紊乱而一张一缩,内衣勒在身上,不断被摩擦出的疼痛提醒着她:“你还活着”。
那只手在她的肚脐附近停了下来。皮肤因惊恐而开始微微抽动,那是腹直肌在本能地躲避压迫,却又无处可去。
她的眼睛睁得极大,瞳孔紧缩,泪水没有流下来,只是挂在睫毛上,像尚未坠落的雨。
她看向前方,看着那个轮椅男慢慢抬起另一只手——那只手像蜡制的标本,干瘪、畸形,指节嵌在一起,像未完成的雕刻。
他把它伸向她的胸口,动作慢,却极稳。
那一刻她终于发出一声极细的“嗯——”声。
不是反抗,而是某种控制崩解的信号——一个在高压下开裂的玻璃碗所发出的第一道裂痕。
她整个人的意识突然断层。
她感觉不到胸口的布料被触碰,也感觉不到那只手是否接触了肌肤。
她的思维像被剥离,灵魂从皮肤内抽出,站在房间天花板上,看着下方那个身穿白色制服、缩成一团的女孩,眼神失焦,口唇轻颤。
她甚至看到自己的头发因冷汗而贴在脖子上,发梢滴水,在制服衣领上印出一圈圆晕。
她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说的话:“女孩子要学会安静,要乖,要柔顺,才不会惹麻烦。”
她的手仍旧握着对讲器,那手此刻像一具假肢,毫无感觉。被压在下方的手腕已经微微发青,皮肤因久未活动而变冷。
而外界,仍在推进。
那声音,那气味,那一个个细节,在她的意识中越来越远。
她不再听见他们说什么,只听见自己耳膜内“嗡嗡”的声音,像被盖进了密封玻璃罐中的风暴。
她想喊。
她真的想。
可一开口,只有热气,没有声。
向思思并未昏迷。她甚至从未接近失去意识。
她的大脑前所未有的清醒——过度的清醒。每一秒钟、每一个触碰、每一次喘息都像被钉进体内,不断重复、不肯散去。
她清楚地感觉到,那只沾着老年人汗味的手穿过制服的下摆,从腹部缓缓向上滑。
指腹冰凉、指节粗硬,划过她的肌肤时带着一层油汗和老化角质的颗粒感,像钝刀子在擦拭布面。
她能分辨那是粗棉制服与打底棉衫之间微妙的空隙,也能感受到手掌每次滑动时肌肉下细小的震颤。
“Stop,”她几乎是用呼吸说出来的,“pleasestopit。”
声音太轻,像夜里一滴雨砸在玻璃上,根本不足以刺破这间房的沉寂。
她的胸部被压迫着。
轮椅上的人动作缓慢而执拗,指节从领口探入,用一种近乎玩味的力道勾住内衣的边缘,将那原本稳妥包裹住她身体的布料轻轻上提——不是猛拉,不是撕扯,而是“观察”,像是在翻看书页。
她下意识抬手去挡。
她的手臂颤抖,却依旧撑起动作,她的指甲几乎抠进对方畸形手腕的皮肉,但下一秒,那只宽大粗糙的手猛然扣住她的手腕,向下一压。
“Dontmove,littleMissnurse。”声音不重,甚至带点轻快的调子。
她挣不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