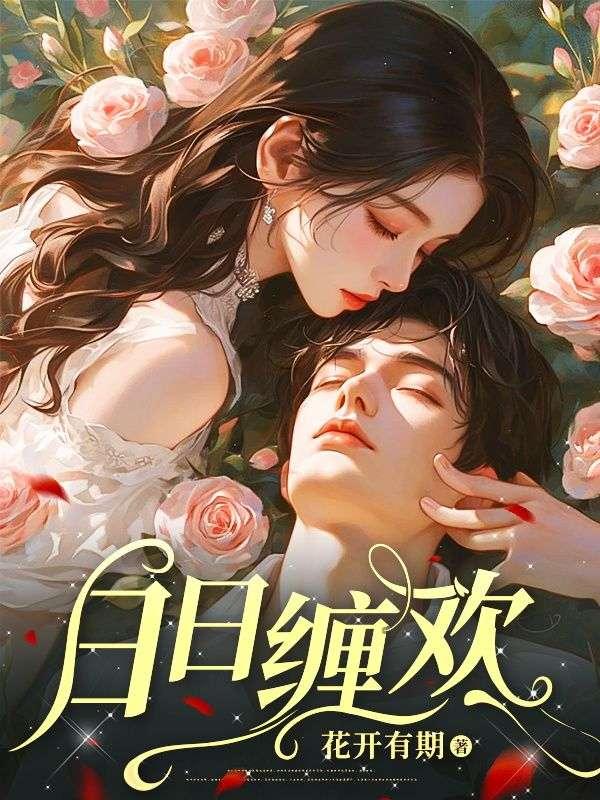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彼岸花落时 > 第12章 封闭的护理室 回忆(第3页)
第12章 封闭的护理室 回忆(第3页)
她的腿被那只手轻轻压住膝盖,往外掰开了一点。只是一点,不足五度的角度,却像是被暴露在烈日下的花瓣,在未开放时就被人强行扒开。
“Don’tbescared,”
“Just…acheckup。”
轮椅上的男人将他的脸贴近她的颈窝。皮肤被呼吸打湿,又被胡渣刮起微痒的摩擦,像细小的针在扎——一根根,不深,却密。
她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发抖。
不是冷,而是那种极度紧张之下,全身神经释放出的无序信号,像战栗,又像哆嗦。
她能感受到自己的肌肉在下意识做出“逃”的准备,可脚步、膝盖、腰、肩,全都被锁在原地,无一能动。
“Please,”她声音再次从喉咙挤出,几乎比呼吸还要轻。
他们听到了。
但没人停。
侏儒那只手终于探入了裙摆下沿。
他并未直接侵入,而是沿着她压缩袜与皮肤交界处慢慢划圈,每一圈都带着奇怪的耐性,像是品尝某种咀嚼需慢的甜点。
那触感混合着粗糙指腹与汗液之间的湿意,一点点溢进她身体最敏感的边缘。
她终于用尽最后的力气,猛然向侧边一拧,想从缝隙中脱身。
可才一动,膝盖撞在床沿,疼痛袭来,她整个人反而摔坐回床角。
那人顺势压了上来,手臂横在她胸前,用力稳住了她。
“Don’thurtyourself,MissNurse。”
他们笑着说话的语气,是调情式的哄骗,却比命令更让人恐惧。因为它假装“柔和”,假装“一切都在好意中发生”,假装“你也默许”。
她的眼神涣散地望向天花板。那道裂缝像是在笑,笑得弯曲扭曲,像一只张开的口袋。她的胸腔剧烈起伏,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
她甚至开始怀疑,是不是自己没有拒绝,是不是这场发生的事,不足以称为“异常”。
她大脑里闪过项目安排时那封信的用语——“表现优异的跨文化护理学生代表”。
她想起导师的微笑、宿舍同学的羡慕语气,还有护士长那句:“Room12需要一个安静的亚洲女孩。”
是的——安静。
她正“表现得”很好。
侏儒正蹲伏在她膝前的位置,近到她几乎能看到他皮肤上细小的毛孔——那些因年久失养而堵塞的毛孔鼓起一个个灰白色的小点,皮肤泛着黄腻的油光,仿佛长年泡在某种胶质空气中,呼吸不到氧。
他的呼吸声近在咫尺,鼻翼翕动,仿佛在品味她皮肤下散出的每一缕温度与气息。
“Softskin,”他低语,“likepetals。”
那语气像是咀嚼糖果前的赞叹。可他眼里没有光,只有浑浊粘稠的贪婪,像污水池中飘着的油膜。
他身上有种味道——不是常规的汗臭,而是湿腻、闷腐的旧布味,像长年未换的棉被,在湿热天气中长出的霉丝。
他衣领内的皮肤泛着斑斓的红紫斑块,胸口塌陷,锁骨高高耸起,像两根要刺穿皮肤的钝骨。
而轮椅上的人,静静地靠在她另一侧,像影子。
他的头发稀疏,贴在头皮上,泛着灰白色的油泽,仿佛只剩下最后几根挣扎在光线下。
他的牙齿斜出嘴角,露出一口不整齐的黄褐色残齿,嘴唇干裂,偶尔舔一下,留下一圈深深的唾痕。
他们与她,几乎不是同一个世界的生物。
而她……
她的皮肤白得发亮,是那种健康日照下生出的淡粉透明感。
压缩袜将她的小腿轮廓包裹得紧致有型,线条笔直,从膝头以下一直到脚踝,宛若模具中倒出的蜡像。
她的腿在抖,轻微而节奏不一,那是神经末梢不受控的应激放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