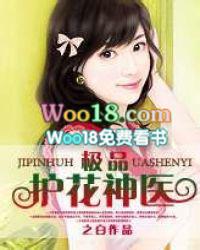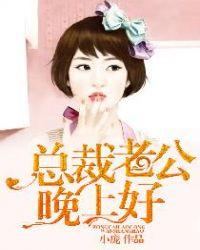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穿书给权臣冲喜后 > 170180(第12页)
170180(第12页)
这个时候,田守朴指挥着差役将县衙备的晚饭抬上来。很简单,每人两个糙米饭团,一碗飘着菜叶子的米汤。但对一直喝稀粥的众村民来说,饭团已经是好东西了。
田守朴和李震士没离开,往马扎上一坐,同样跟着众村民一同吃饭团。
孙铁牛这回坐在里圈,前面隔着一排差役就是两个朝廷命官。大概是田李二人的行为让人感到亲近,孙铁牛大著胆子问:“李令,您家里种过冬油菜吗?收成有多少?”
李震士咽下一口米汤,却没有答,而是笑着问:“你们看《旬报》不?”
江南的村子不遭灾时过得还不错,基本家家户户都会送孩子到学堂认几个字,不一定能看得懂多少,但名字和数字总得知道。在这种风气下,期期送到村里的《旬报》,自然大家都知道。
李震士看众人表情便知答案,继续说:“今年河关那边开了新田,你们知道吗?”
河关,是距离江南遥远的边关。江南的村民自己的生计都顾不过来,哪里会关心到河关的事。
不过,江南文风胜,每个村都有人正式进学,也总有人留在村里。这种时候,村长必会带这类人来做记录。这些人中就有关注得多的,比如孔仁。
孔仁接话:“我记得《旬报》上登过,河关开的田种的是高产新稻种。”
随后也有几道声音附和他。
李震士点头:“河关的田是军屯,就是我带着农学署的人去教导那些边军种田。你们猜一猜,那高产稻种亩产有多少。”
周围听到的众人都愣了下,相互看看,没敢说话。
孙铁牛胆子大,犹豫片刻,先说:“三百五?”
他不记得在哪里听说过,北方虽有能种稻的地方,但产量会比南方低些。加上新田和新手,哪怕是高产稻种,伺候不好也得不了多少。
江南都种稻,这里的人对稻谷产量都熟得很,三百五十斤已经是看在“高产”二字上往高了说。便是江南,如果是开荒,头一年二百多是常态,能有个三百斤的亩产都能笑掉牙。
李震士只笑着,先没说话。不过那表情,一看就知道孙铁牛没说对。
有人被孙铁牛带得胆子大了,跟着猜:“不会能有四百斤吧?新田啊!”
李震士伸出一只手,五指张开,一字一字说:“平均亩产五百多斤。你们可以留意《旬报》,最近就会登。”
这数字是姬安悄悄给他透露的。李震士自己算着时间,感觉河关还没能报得上来,不过他听说上官钧的庄子也种了几亩,猜测可能是那里的数据。而且姬安还说会登在《旬报》上,他也就拿来用了。
四周围顿时响起一片片的抽气声。
闲聊不像刚才讲课,李震士声音不多大,坐得远的没听见。内圈把话往外传,外圈就又发出一片声响。
“不可能吧!我们江南最好的良田,顶了天也就亩产四百五十斤!”
“四百五我还只是听过,没见过呢。我家的田最多收过四百二三,丰年平年拉平来算,差不多三百七八。”
“要头一年真能有五百多,那等田种熟了,亩产岂不是能上六百斤?”
这句说得大声,李震士听见了,回道:“我也是这么估计,两三年后该能到六百斤。那么,参照以往南北稻谷产量差别,那稻种换到江南来种,亩产估计能有八百斤。”
这回的抽气声更大。
八百斤!岂不是直接翻一倍!
李震士又描述起河关的新稻,讲得非常详细。江南的农人对水稻再熟不过,越听越觉得可信。
孙铁牛大著胆子问:“李令!那能在我们这儿种吗?”
李震士淡定道:“圣上是打算在江南推广。如果这回冬油菜种得好,圣上放心你们,我想应该会优先考虑给你们种。”
四周众人听了,连连保证会努力种好冬油菜。
等吃过饭,天色渐暗,田守朴让人点上火把。李震士再次和众人复习了一轮下午的要点,让众人尽管提问。等解答完问题,这次教学才算彻底结束。
这时,田守朴站出来说:“大家先跟我来一下。”
他没说去哪,不过众人今日被县衙招待得挺好,没多问就起身跟着走。
田守朴领众人去了明日分种子的仓房。
他让人将各仓房门都打开。
火把之下,所有人都看得清楚。
仓房里空空如也,只有地面依稀像是贴着张符纸。
众人非常不解,低低的吵嘈声响起。
“不是明日发种?怎么还是空的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