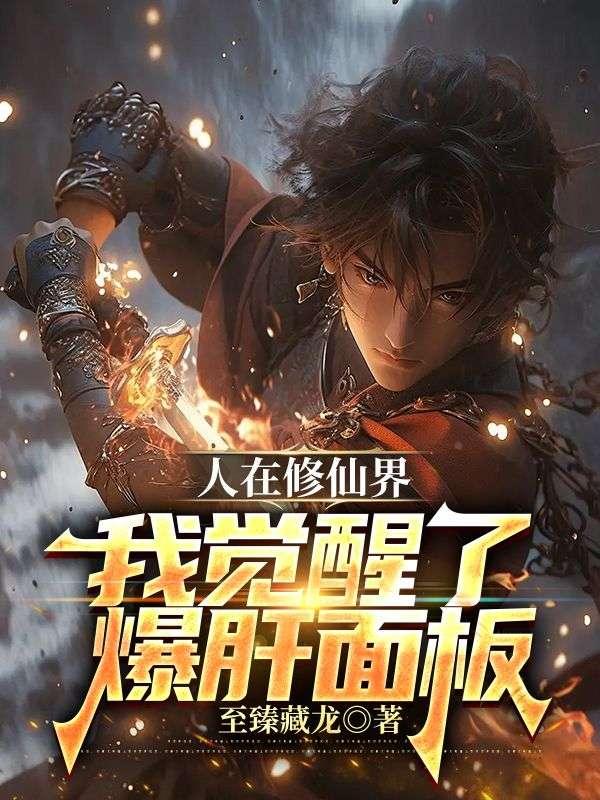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反派夫君又疯又狗 > 3040(第15页)
3040(第15页)
表皮的伤口都如此,更何况被穿投的渊深里处,更何况被剧毒的毒液大量汩汩浸透过。
只怕,里头的嫩肉都已经是被侵蚀腐烂了。
阮流卿愈想,心跳得更快,又是害怕又是羞赧,泪水在眼眶里打转,却迟迟可以落下来。
她不知道晏闻筝有没有察觉他如此的情绪,却能感受到他已遒劲的握住她脚踝分开。
深夜的凉意渗透,阮流卿感受到伤口都在不住瑟缩。
而今没了视觉,可其他感官却异常敏锐。
她听到清脆的瓷瓶被剥开的声音,重重的敲打她的心魂,而后,很迅速,却似乎又带着同晏闻筝极不相称的柔意,将药抹在她的伤口。
当真触碰一瞬,阮流卿全身发抖,可晏闻筝似早已料到,牢牢的压制。
阮流卿咬着被子流泪,若雨后秋叶哆嗦着,却倔强的不肯哭出声来。
微凉的膏药渗透发热红肿的伤口表皮,阮流卿敏锐的感受到清爽的凉意,可蛇毒还尚存伤口内里,恐怕只能……
果然,在下一瞬,淬着膏药的指节循循,阮流卿紧咬着牙关,难忍的没忍住闷哼出声来。
声音很低,很委屈,从被子里闷出来,若羽毛般在晏闻筝心底拂过,他微蹙着眉,心
里又泛出那道烦闷,可从嘴里吐出来的话仍是残忍的冰冷。
“娇气。”
他手上动作没停,涂抹着膏药,却能感受到重峦叠嶂的绞杀。
他眼眸微眯,定定凝视着,漆黑瞳眸倒映着绯透无暇。
干净,纯粹。
可早就脏了。
被自己弄脏了。
他轻嗤出声,眸光转而黑得骇人,却依旧只上着药。
时间一分一秒的捱过去,阮流卿全身都泛出了粉色,抖得不成样子,泪水洇湿了被褥。
膏药总算里里外外将那日毒蛇獠牙穿透过的伤口覆盖了,晏闻筝收手,竟是有些艰难。
恍若初拨开瓷瓶瓶口似的“啵”的一声,晏闻筝眸暗得更深,扯开少女覆在面目上的锦被,清清楚楚看见其脸蛋上的泪痕。
很多的泪,想必从上药之初,便在哭了。
他抬眼看着,徐徐,凤眸微上挑,带着恶劣的戏谑,“这么多水?”
这句话,阮流卿听见了,反应了一会儿晏闻筝在鄙夷什么,才想起是她嫌弃自己哭哭啼啼,将他的被子洇湿了。
她更是委屈和恼怒,可再无暇同他争执,泪眼汪汪的瞪着他。
没曾想,他竟在她的注视下,缓缓抬起他的手来。
骨节凌厉修长,冷白的色泽极具美感,然可惜这是一只杀人的、恶魔的手。
漂亮的指节在朦胧的烛灯下泛着柔和,可阮流卿却能看见其整根食指上尽数透出的晶亮水痕。
那上面淬过膏药,可而今如此,分明不是膏药使然——
阮流卿紧紧咬着下唇,顿时哭出了声,脸涨得通红。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她憋不出什么骂人的话来,可晏闻筝却似很愉悦,不以为然的轻笑,妖邪又狂妄。
甚至要将她抱进怀里,阮流卿哭着挣扎可全身没什么力,更何况晏闻筝这样插翅难飞的囚笼。
他噙着笑,箍着她的腰,一手由一下一下抚着她的后脑,穿过她的青丝。
“好了,卿卿。”
低沉的声音轻缓,甚至勾着难言的耐心很宠溺,似如真的在哄一个爱撒娇的小孩子一般。可唯独,他没有半分真情,只是兴致上来对自己猎物的半分馈赠。
“这几日是我疏忽了。”
他边说着,又亲蹭她耳朵尖,阮流卿又气又急,看着眼前近在咫尺的颈项,念从心生,将自己的齿关覆了上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