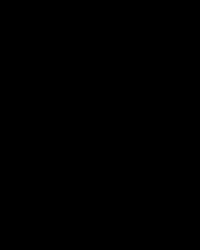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孤廷 > 旧信(第2页)
旧信(第2页)
他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在接近自己?
“郡主?你想什么呢?”阿慎探过头看她,“这信不看看吗?我瞧柳文昱宝贝似的抱怀里,给我的时候还怪舍不得的。”
洛芾手指下移,慢慢划到锁扣,将盖子掀开一条缝又立刻合上。
墨儿瞧她脸色不对,悄悄拉着还要凑上去再问的阿慎出了门。
刻漏的滴答声回响在耳边,洛芾的手指一下接一下的敲在木盒上。
和害怕相比,好奇终归略胜一筹。
食指挑开盒子,答案近在眼前。
是一摞叠的整整齐齐的信。
洛芾的心跳愈发剧烈,胸腔的震动传遍全身,泛黄的信纸几次从颤抖的手指间滑落。
喉头滚动,洛芾试图吞咽口水压下即将跳出喉咙的心脏。
她从小就临摹母亲的字,只需一眼就能看出,这些信确实是母亲的笔迹。
信是按顺序收好的,最上面的一封写在羲和二十三年,那是洛芾父母成亲的第一年,瞧着像是封回信,信中写着“听闻兄长高中,甚是欢喜”。
大约是这封信之后,他们恢复了联系,每隔几月便有书信往来。
柳文昱似乎常会送些收藏的字画与陆知渝共赏,所以最初信中所言除了书画便是玩乐,字里行间都是掩不住的喜悦。
通信日久,两人看着更加熟络了,陆知渝也偶尔向他发些牢骚。
从永熙二年开始,信中更多了几分仇怨,提起洛珩也不再称呼“阿珩”,只写大王。
到了永熙三年,连大王也不愿写了,每每提及都直呼洛珩。
那一年,因久无子嗣,洛珩迎娶了顾侧妃。
光风霁月的陆家幺女,终究还是低下了骄傲的头颅,那手飘逸张狂的字也变得忧郁。
直到永熙五年八月,陆知渝得知自己有孕两月,雀跃的语气跃出纸面,最后一句写着“我与阿珩皆欣喜若狂。”
不知不觉看空了盒子,只剩下最后一封握在手里。
信写在永熙六年元月,那是洛芾出生的前一个月。信中一笔一划都宛如针尖麦芒,刺痛了洛芾的双眼。
洛芾稳下心神逐字逐句的去读,三四张的信纸分明都是熟悉的字迹,可淡然的语气说的却像是旁人的故事。
“恍惚想起初嫁他那年,我固执的以为相爱就足够了。”
“真是应了父亲哪句话,他确不是那个不名一文的少年郎了。”
“他心里有了算计,连爱也成了筹码。”
“知渝无颜再见父兄,留此绝笔于兄长,勿语旁人。”
旁的字句洛芾都一跳而过,唯有一句被她反反复复的看。
“他真的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我喝了几个月的毒药。”
母亲知道自己被下了毒?
这算什么?为了和一个男人赌气赌上了自己的命吗?
父亲竟不是因为她的病才知道母亲被下了毒吗?
原来他早早的就知道,他不是没有帮母亲报仇,而是害死母亲的帮凶。
母亲的爱成了他算计的筹码,那她又算什么呢?也是棋子吗?
百爪挠心,头痛欲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