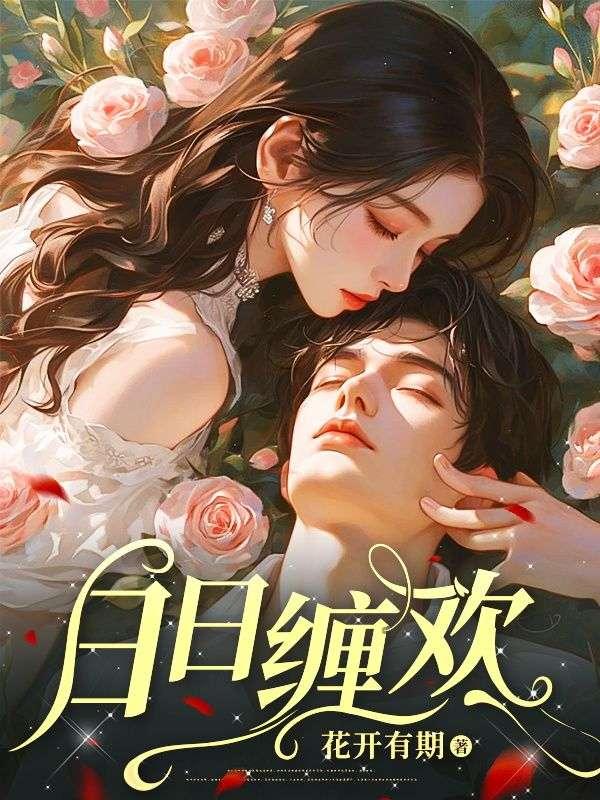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重回灾年给老妈完美童年[七零] > 第 4 章(第2页)
第 4 章(第2页)
“玉米!是玉米!”成秀英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,扑过去抓起一把,浑浊的老泪再次滚落,“老天爷……老天爷开眼啊!这是……这是震前刚换回来的口粮!压在柜子底下,没……没被埋实!”
成秀英看着那半瓮玉米,又猛地回头看向靠在炕边、脸色苍白如纸却刚刚救了弟弟一命的方夏荷,以及她身边那个怯生生指出了粮瓮的小女孩何田。
她紧紧抱着那瓮玉米,看向方夏荷母女的目光,复杂到了极点,最终,那层坚硬的外壳似乎裂开了一道缝隙,露出里面一丝极其罕见的、属于人情的温度。
“有粮了……”成秀英的声音低沉,带着哽咽:“省着点,掺着野菜……能撑些日子。”
王君顿了顿,目光扫过哽咽的成秀英、重伤的成刚、虚弱的方夏荷、年幼的何田和自己的两个孙女:“天塌不下来!只要人还在,就有法子活!”
昏暗摇曳的灯火下,这句低低的话语,像一颗火星,落入了这片被绝望浸泡的废墟,点燃了第一缕微弱却真实的希望。
王君那句“天塌不下来”还带着颤音在昏暗的厨房里飘着,成刚一声痛苦的呻吟就把这点微弱的希望又扯紧了。他灰败的脸上泛起不正常的潮红,呼吸又急又浅,伤口处被盐水狠狠冲刷过的皮肉,在煤油灯下泛着一种危险的、湿漉漉的暗红。
“烧得更厉害了……”方夏荷撑着炕沿,指尖冰凉,声音带着脱力后的虚浮,“光这样不行……得消炎药,退烧药……不然……”后面的话她没说,但盆里那些脓血污物的气味,和成刚越来越急促的呼吸,像冰冷的针扎在每个人心上。
成秀英抱着那瓮玉米,手臂勒得死紧,仿佛那是弟弟的命。她猛地抬头,目光像淬了火的刀子,射向门外无边的黑暗:“我去找!公社卫生院!黑市!总能弄到!”
“公社路塌了,没车靠两条腿走到天亮也未必到!黑市?”王君绝望地摇头,“拿啥换?就这点玉米?人家要的是钱!是票!”
“拿命换!”成秀英几乎是吼出来,眼眶赤红。
“别冲动!”方夏荷按住胸口,压下翻涌的眩晕感,强行集中精神,“药……肯定要弄,但不能硬闯。秀英姐,你男人……方文斌同志,不是在大队帮忙吗?他……他能不能想想办法?大队……有没有应急药品?或者……他认识的人多……”
“方文斌?”成秀英像是被这个名字烫了一下,脸上瞬间蒙上一层更深的怨愤和绝望,“他?他心里只有他的大队!他的公家事!亲小舅子快死了,他人在哪儿?!”她的声音尖利,带着积压已久的委屈和愤怒,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。
就在这时,院子外传来一阵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,伴随着一个男人粗哑的喘息:“秀英!秀英!家里咋样了?刚子呢?”
一个高大的身影带着一身寒气和水汽,猛地撞开了厨房那扇摇摇欲坠的破门板。来人正是方文斌。他浑身泥泞,裤腿湿到膝盖,脸上带着疲惫和焦急,手里还拎着半截撬棍。
“文斌!”王君像是抓住了主心骨,声音带了哭腔。
方文斌一眼就看到了门板上昏迷不醒、脸色通红的成刚,还有地上那盆触目惊心的血水污物。他瞳孔一缩,几步抢到门板前:“刚子!刚子!伤这么重?咋弄的?”
成秀英却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,猛地冲上去,狠狠推了方文斌一把:“你还知道回来!你死哪儿去了!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!刚子被砸的时候你在哪?!现在回来有什么用!他快烧死了!药呢!你有药吗!”她的拳头雨点般落在方文斌沾满泥浆的胸膛上,哭骂声撕心裂肺,连日来的恐惧、委屈、绝望,在这一刻彻底爆发。
方文斌没躲,硬生生受着妻子的捶打,脸上是深深的愧疚和痛苦:“秀英……秀英你听我说!东头塌得厉害,压了好多人,我……我脱不开身啊!刚子……刚子他……”他看着小舅子那可怕的伤口和灰败的脸色,声音哽住了。
“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!”成秀英打累了,瘫坐在地上,捂着脸痛哭,“药!药啊!没有药,刚子就完了……”
方文斌抹了把脸,泥水和汗水混在一起。他蹲下身,仔细看了看成刚的伤口,又摸了摸他滚烫的额头,眉头拧成了疙瘩。“伤口……处理过?”他有些惊异地看向旁边脸色苍白、靠着炕沿的方夏荷。刚才混乱中,他隐约听到是这个陌生女人在指挥。
“是这位夏姑娘……用盐水……硬生生冲干净的……”王君哽咽着解释,看向方夏荷的眼神充满了感激和后怕。
方文斌看向方夏荷,眼神锐利而复杂:“你懂医?”
方夏荷强撑着站直了些,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:“以前……学过点护理。伤口感染很重,高烧不退,必须用消炎药,不然……破伤风或者败血症……”她用了这个年代更让人恐惧的词。
方文斌的脸色更加凝重。他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。大队那点可怜的急救药品,早就被搜刮一空用在更重的伤员身上了。黑市……他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空瘪的口袋。
厨房里陷入一片死寂,只有成刚粗重的呼吸和煤油灯芯燃烧的噼啪声。绝望像冰冷的潮水,再次无声地漫上来。
“文斌……”王君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,“你……你不是认识……粮站那个老李吗?他路子广……能不能……”
方文斌眼神剧烈地闪烁了一下,似乎被戳中了某个隐秘的开关。他飞快地扫了一眼厨房里的其他人,尤其是方夏荷和何田这两个“外人”,嘴唇抿得死紧,脸上掠过一丝挣扎和犹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