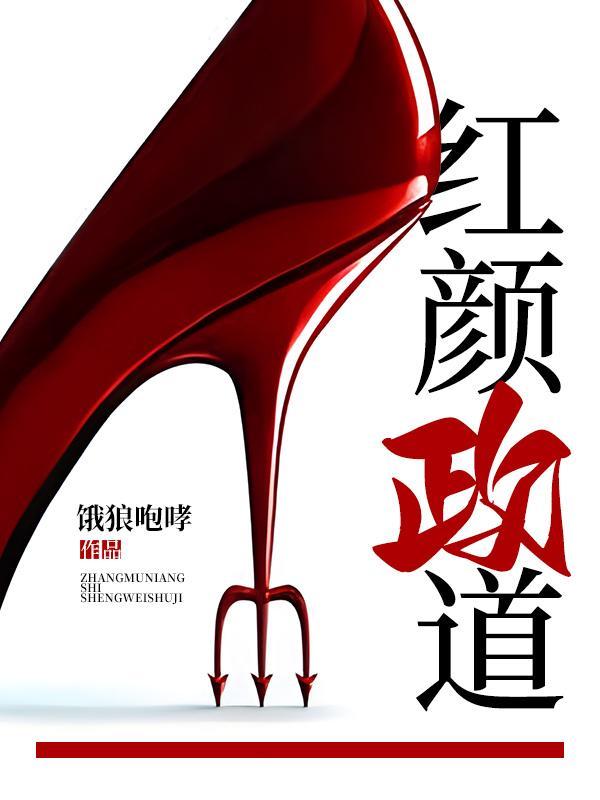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重回灾年给老妈完美童年[七零] > 第 14 章(第2页)
第 14 章(第2页)
已将近晚秋,河水渐渐凉了,方文静搓着手从河边洗完衣裳回来,刚走到村口老槐树下,几个半大不小的皮猴子远远瞧见她,嬉皮笑脸地起哄喊起来:“疤脸婆!疤脸婆!没人要的疤脸婆!”
方文静脚步一顿,脸色煞白,端着木盆的手指僵了又僵。
杨立业扛着一大捆新劈好的柴禾,正从岔道走过来。喊声清晰地钻进他耳朵里。他脚步猛地停住,缓缓转过身。那双总是沉静无波的眼睛,无声地、沉沉地扫向那几个喊叫的孩子。没有怒吼,没有斥骂,只有一种无声却极具压迫感的威势,像一块巨石骤然压下。
那几个孩子被他看得头皮发麻,嬉笑僵在脸上,讪讪地互相推搡着,像被掐住脖子的鸡鸭,一溜烟跑没了影。
方文静站在原地,看着那个沉默地挡在她与汹涌恶意之间的高大背影,一股久违的、被小心守护的暖流,悄然淌过她的心房,酸酸涩涩,又带着奇异的安定。
“谢谢你,立业。”她声音微颤,又格外正式地道谢。
杨立业转过身,对上她的眼睛,眼神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,只是深处似有柔软。
他摇摇头,声音低沉而清晰:
“谢什么。小时候,是你护着我。长大了,该我护着你。”
这句话像一把钥匙,“咔哒”一声打开了尘封的记忆匣子——
“没爹没娘的野种!”
“扫把星!”
打谷场上,小小的杨立业被推搡得踉跄,小脸憋得通红,拳头攥得死紧,指甲几乎嵌进肉里,却倔强地咬着下唇,一声不吭,只有那双黑沉沉的眼睛里,压抑着屈辱。他总是沉默不语,眼睛却倔强得惊人。
那个扎着褪色红头绳、穿着旧棉袄的小旋风冲了过来。小方文静使出吃奶的劲儿狠狠推开领头那个大孩子,张开细细的胳膊,像护崽的母鸡一样,死死挡在杨立业身前,小胸脯气得一起一伏,仰着小脸,声音又尖又亮,“你们不许欺负人!他是我的人!再敢碰他一下试试!”
幼时的方文静虽然是“孩子王”,面对比自己年长几岁的大孩子终究吃亏。方文静护着杨立业,因而率先挨了两拳,痛得她哇哇大哭,哭声嘹亮,这哭声让小立业不知所措,只好陪着哇哇大哭。
他很少有这样大哭的时刻,他幼时的很多情绪来源于对小文静的模仿。
那时的她,小小身躯里爆发出惊人的勇气,像一道明亮的光,照进了他的童年。而他,被不自觉牵引着,成了她的小跟班。
方文静一路走回家,心绪像被风吹乱的柳条,摇摆不定。那芝麻烧饼一人一口,最后只剩下油纸包,油纸包的香气和残留的体温,与记忆里覆盆子的酸甜滋味交织在一起,在她心头反复冲刷。
几天后的傍晚,夕阳将天际染成一片绚烂的橘红。方文静正在自家小院里费力地劈着几根用来引火的细柴,动作有些生疏。汗水顺着额角滑下,浸湿了鬓边的碎发,也洇湿了左颊疤痕附近的皮肤,带来一丝浅淡的刺痛。
她咬着下唇,高高举起柴刀,却因为姿势不对,力气又小,柴刀落下时偏了,“哐当”一声砸在石头上,震得她虎口发麻,柴火却纹丝未动。
院门口传来熟悉的脚步声。杨立业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那里,肩上似乎还带着刚从地里回来的尘土气息。
方文静的脸“腾”地一下红了,慌忙放下柴刀,下意识又想侧过脸去,手指局促地绞在一起。
杨立业没说话,只是大步走过来,动作自然地接过了她手里的柴刀。他粗糙的手指不经意间擦过她微凉的指尖,带着薄茧的触感让方文静指尖微微一颤,飞快地缩回了手。
“我来。”他只说了两个字,声音低沉平稳。
他站在她刚才的位置,高大的身影几乎将她完全笼罩在自己的阴影里。
他微微屈膝,腰背绷紧成弧度,手臂肌肉在洗得发白的旧工装下隆起。他目光专注地盯着地上的柴火,手腕一沉,柴刀带着一道干脆利落的弧线精准劈下——“咔嚓!”一声脆响,柴火应声裂成两半,断面光滑整齐。
方文静站在一旁,看着他专注的侧脸,黝黑的皮肤在夕阳下镀着一层暖金,鼻梁高挺,线条冷硬。
他没有立刻停下,而是沉默地将剩下的几根柴也利落地劈好,码放整齐。整个过程行云流水,没有一句多余的话。
“好了。”他直起身,将柴刀递还给她,目光落在她微微泛红的虎口上,“下次小心,别震着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