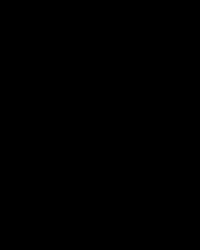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我在武侦社当画师的日子 > 是夜(第2页)
是夜(第2页)
四月中下旬的横滨仍然存了点凉意,夜里只穿单衣会有些冷。我画了一件披风裹在身上,跟着太宰走到路口,只见远处的路灯照亮了雪白的樱花。
春天,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。
“几天不见,居然已经开了这么多。”太宰望着那连绵的白,淡笑道,“小君之前来过横滨吗?”
“来过。我住在东京。”
“喔,很近呀。想不想回去看看?”
“那又不是我生长的东京。”我耸了耸肩,“对我来说,哪里都是一样的。”
探照灯远远地打过来,计程车在空旷的路面上飞驰而至,急促地停在我们跟前。
太宰这回坐在了副驾驶。
今天他罕见地沉默,一路上连姿势都没怎么变动,双手插进口袋,膝盖微微张开,后视镜里映出一只低垂的鸢眸。
他的目光不知在看哪里,也许什么都没看。
我坐在后座,昏昏欲睡。
司机也一直不吭声,行使在空无一人的小路上,一侧是漆黑的树林,一侧是无光的房屋。
忽然,车辆猛地一歪,我的额头重重地磕到车窗上,一下子惊醒了。
前排传来打斗的动静,又是“咔哒”一声脆响,很像枪械拉保险的声音。
我茫然地睁开眼,发现太宰不知何时已经举起手臂,手里握着一支铁灰色的手枪,枪头直指司机的太阳穴。
右侧的后视镜里,映出司机惊恐错愕的脸。
“几个人?”太宰冷冷地问。
“只……只有一个……”
“真是麻烦啊……”
我迷迷糊糊地听着他们对峙,不知道太宰又说了什么,那个四十多岁的司机直接被吓哭了,老老实实地开着车往最近的警署行驶。
后来,车辆边围了一堆人,司机被拷走了,他们好像从后备箱翻出了一个被药物迷晕的少女。
太宰敲了敲车窗。我透过窗玻璃,看见他笑得无奈。
“好啦,回去再睡。真是的,差点被人拐了还不自知呢。”
我慢吞吞地从车里爬出来,被警署的明亮灯光刺得睁不开眼。
“……太宰先生在这里,他还敢动手吗?”
太宰摸了摸下巴,竟也有些困惑。
“嗯?也是啊,我毕竟是男性……”
我揉了揉眼睛,抬起头打量了他一阵。
秀气的脸、流浪汉似的发型、完全称不上强壮的身躯、浑身像烧伤病人一样缠满了绷带。
好吧,确实不像什么难对付的人,即使是男性。
反倒像是在欧洲地铁里会被老太太塞钱的可怜虫。
太宰掩唇打了个哈欠:“真讨厌,本来这个时候该到家了。好困啊,想喝酒。”
我转头环视,发现路对面有一台自动贩卖机。
“那里应该有卖罐装啤酒。要去买一瓶吗?”
“不要。”太宰撅起嘴,“那种酒不好喝。我想喝加了冰块的清酒或苹果酒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