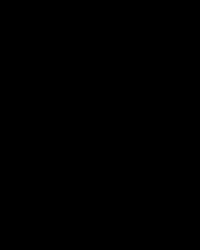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重生后成夫君妹妹 > 012(第2页)
012(第2页)
王美人好奇的发问打断她思忖,灼玉回神,随口道:“在看各位夫人们的裙摆,花样都很好看。”
王美人挑眉笑笑:“论裙衫样式,就属季美人和玥翁主的独特,谁让季美人生了一双巧手?不过我若有个像两位翁主这样的女儿,也得日日苦学绣工,变着法做衣裳。”
季美人神色闪过几分不自然,谦逊道:“闲来无事时绣的一点小玩意罢了,称不上多独特。”
众人就首饰衣裙聊开了,灼玉若有所思敛下眸。
-
见完宗妇后,她记着容濯的话,主动去了宜阳殿。
容濯一身玄色绣金深色,着远游冠,腰佩绶带,显得格外庄重,含笑给她新年礼:“王妹新岁安康。”
灼玉打开檀木盒子,是块金锭,模样肖似戒尺,上方刻着‘敏而好学’,充满了对她的讥讽。
再看容濯,玄色深衣削淡他周身温润,衬得他似只笑面虎,眸中笑意也像温柔刀。她迎上他含笑目光,挑衅道:“多谢,我喜欢金子,虽说不够矜雅,但正衬我这个俗人。”
容濯嘴角微微上扬:“今日正旦,不唤声阿兄听听?”
灼玉关上盒子,神色有些微不自然:“昨夜多谢你救了我,我欠了你人情,日后再还。”
重生数月,她第一次对这位兄长落下浑身的利刺。
但唤阿兄,她还做不到。
容濯低垂的鸦睫如折扇,阴影遮住眼底神色:“那便欠着,终有一日我要听到王妹唤一句阿兄。”
他揭过此事,问:“昨夜为何撞见薛相却不回避?”
灼玉反问:“你又为何刚好出现,别说偶遇,我可不是傻子。你是在跟踪薛相,还是跟踪我?”
容濯望着她眼眸:“你。”
面对她倏然戒备的神情,他并未收敛,继续道:“王妹自幼傲气,绝不会与厌恶之人往来。而薛炎跋扈、恃强凌弱,绝非王妹会欣赏之人。既如此,为何还要与他往来?”
灼玉敷衍应他:“因为孤独。”
“孤独?有两位亲兄长在,何需什么炎阿兄?”容濯轻嗤,“为兄猜测,你是不知从何处得知当初薛邕不曾救回姜夫人,对此存疑,从而接近薛炎,想利用他对付薛相。”
他的话让灼玉越发警惕,反问他:“若我想对付薛相,你会如何,是和父王告状,还是睁一只眼闭眼。”
亦或与她同谋?
容濯颀长的身形立在她面前,似一株能遮住风雨的挺拔青松,他学起她答非所问:“不妨先猜猜,若薛炎犯了错,薛相会如何?”
之前灼玉猜不出,但近日她有了数:“会牺牲薛炎,大义灭亲?”
“不错。”
薛炎这条路果真行不通,好在灼玉早已放弃,问他:“倘若薛相的私情暴露了,父王会重惩他吗?”
刚问完她已猜到。
眼下父王心中只有阿娘,恐不在意宫妃红杏出墙,至多介意君威被挑衅。可若薛相再寻些“苦衷”,搬出救命之恩,父王指不定会原谅。
灼玉颓丧垂头。
容濯见此,宽慰她:“父王念旧,薛相救过父王且近年励精图治,并无过错,我们还需另觅契机。”
“我们?”
灼玉捕捉到了关键的一句:“难不成你还打算出手帮我?”
容濯没回答,先抛给她一个问题:“帮你义务不可,但你需先告诉我,为何非要扳倒薛相?”
灼玉编了个容濯会在乎的理由:“我偶然偷听到薛相说要卸掉大兄兵权、掌控赵国。”
后半段话其实是前世从容濯那听的,某次春深之后,她双手按在容濯胸口,在他怀中支起脑袋,问:“你的城府很深,听闻长公子亦骁勇,怎会让薛邕那老狐狸夺了赵国大权?”
餍足后,容濯心情颇佳,指腹一节节地描摹她的脊骨,眸中温存缠绵:“我少时多病,常年在外求医,前几年被天子选为皇太子伴读,因远离赵国,对政务不甚熟悉。长兄善武却不善文,父王亦然,便把文政都交给薛相,这才给了他可乘之机。”
她再问:“薛相既然这样厉害,怎不早几年夺权?”
这才从容濯那得知是因为容铎手握兵权,薛邕不得不忌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