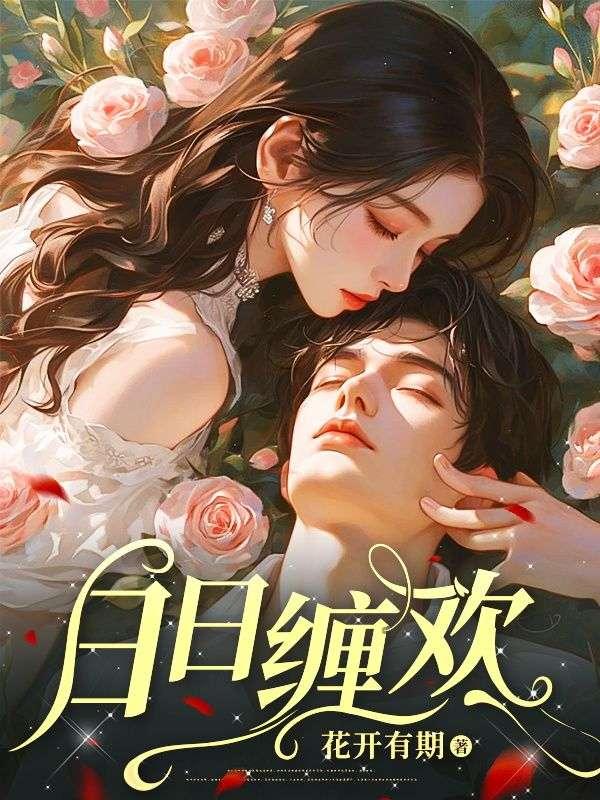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囚云阙 > 第 98 章(第3页)
第 98 章(第3页)
沈卿云伏在地上的身子几不可察地僵了一瞬。
父亲告病,改制推行受阻,楚家施压未减,而她的婚事悬而未决……所有的线头,此刻都被皇帝看似随意地捻在了一起,摆在了她的面前。
清凉殿内,水汽氤氲,凉意透骨。
可沈卿云却觉得,自己正被架在火上缓慢地烘烤。那甜腻的香气不知何时已淡去,或许是被水汽冲散,亦或者只是她的嗅觉已然麻木。
她依旧没有抬头,声音从紧贴地面的唇间逸出,带着压抑后的平静,甚至比方才更稳了些:“陛下体恤臣父,臣感激涕零。父亲常教导臣,为臣者,当以国事为重,自身为轻。臣……亦不敢忘。”
话音落下,殿内又是一段令人心悸的沉默。
就在这近乎凝固的气氛里,沈卿云继续禀告:“臣近日处置养病坊一应事务,深感阻滞,尤以北方边陲为甚。”
她顿了顿,语速平缓,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件公事:“彼处连年受战事侵扰,民生本就凋敝,更兼有不良商贾借地利之便,囤积居奇,蓄意哄抬药材市价,以致疫病防治,困难重重。先前派往北地的医官,屡有奏报,俱是进退维谷,有苦难言。”
说到此处,沈卿云将额头从冰冷的地面上微微抬起一寸,依旧保持着跪伏的姿态:“臣斗胆,恳请陛下降旨,准许臣……亲赴北地,督办药材平抑,疫病防治之事。”
远离京畿权力中心,前往苦寒战乱之地。这看似是主动请缨,为国分忧,实则是在这盘死局中,以退为进,远离眼前这令人窒息的天子权衡与后妃倾轧。
到底是被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境地。
无法任凭自己彻底臣服于皇权,将所有一切都献祭给这盘冰冷棋局,成为一颗完全听凭摆布的棋子。
她什么都做不到。
做不到扭转乾坤,做不到保全所有,做不到在权力的碾压下毫发无伤,更做不到违背本心。
她唯一能做的,便是在这看似必输的棋局里,用近乎自伤的决绝,为自己争得一个不那么屈辱的落子之处。
景昭却始终不曾开口应允或拒绝。
死寂的殿内,只有他修长指节一下一下叩动那只白玉炉盖的细微声响。
清脆,规律,敲打在人心上,比任何呵斥更令人心头发紧。
他在权衡。
权衡她此举是真心为国分忧,还是以退为进的姿态。权衡放她离去对制衡楚家,安抚沈家有几分好处。权衡这枚一度颇为趁手的棋子暂时离开棋盘,会否影响接下来的布局。
而她,只能匍匐在地,将所有的希冀与命运,寄托于帝王心中那点微不足道的怜悯之上。祈求这份怜悯,能让她在清凉殿内全身而退。
直到那缕令她心惊胆战的甜腻香气,再度无可回避地袭来,丝丝缕缕,缠绕鼻端。
沈卿云的心,在那瞬间沉到了底,泛起刺骨的绝望。
原来如此。
终究还是逃不开么?
从一个看得见的囚笼挣扎而出,却要坠入另一个更为庞大,也更令人窒息的囚牢之中?她的余生,难道注定要与这些无尽的算计、倾轧、虚与委蛇纠缠至死?
每时每刻,连闭上眼后的黑暗里,都不得片刻安宁与解脱?
锦靴踏至她跟前停下。
随之而来的,是自上而下,近乎实质的审视目光,沉重地笼罩住她微微颤抖的脊背。
“爱卿为国分忧,其心可嘉,朕心甚慰。”
不知过了多久,帝王平静的嗓音终于再度响起:“准了。”
沈卿云浑身一颤,额头重重触地,动作甚至比方才请罪时更加顺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