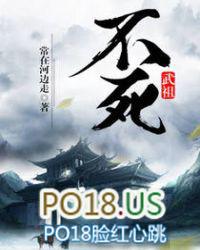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丞相总想扒我马甲 > 英雄救美(第2页)
英雄救美(第2页)
“谁给你的胆子把手伸到我大哥身上?”
“……止不明白小姐在说什么。”一个虚弱的男声响起,是白止。
“呵。”女子意味不明轻笑一声,紧接着便是某种皮质材料与木板的轻微摩擦声响:
“我给了你三个月。”
“这三个月里,我找人买通了中书主事,找了你那个最熟悉的同僚穆朗,你猜他们怎么说?”
“……”一阵短暂的沉默:“…小姐对我起疑,为何不直接来问——”
一声比之前更为迅疾的鞭声打断了白止的话:
“你来问我?”
女子似乎被他这话气得不轻,话末又从喉间气出一声笑音:
“你来问我?——白止。”
女声猛地一转:“你是不是忘了你欠楚家什么,你又欠我什么?你敢让我来伺候你?”
“白止不敢。”这声倒是比先前都要大声了点。
“我看你分明是敢极了!”又是一声鞭响。
想来是不愿再听白止辩解,女声不再出现,取而代之的是一道接一道鞭子划破空气的尖鸣,以及男子喉间压抑的喘息。
终于,在不知道多少声鞭落之后,顾少室总算从暗处走出,扬声:
“楚小姐。”
“参见丞相。”春鹊和方冬忽然见他出来,皆低头朝他行礼,不过方冬却是在得他免礼后睁着一双眼睛企盼着看他,仿佛见到了什么救世神仙,那眼神,就差直接说“公子你快救救白止”。
顾少室轻咳一声,示意她收着点,便接着朝已停了鞭声的车内继续:
“小姐如此滥用私刑,罔顾人命,就不怕遭报应吗?”
奇也怪哉,顾少室竟然没拿刑部那套规矩说事,竟然还说起“报应”来了?楚月安抹了抹嘴角血迹——这当然不是真的,而是近段时日季玉心做出来的假血,她早年和母亲一道在戏坊生活,像这样以假乱真的道具可以说是手到拈来。
但方才的鞭子确实实实在在挨的,他身上虽的确有早年因贪玩偷懒不练武被父亲家法伺候得来的鞭痕,却大多年岁久远又保养得当,消得差不多。
因而为了演好这场戏,这几月里如同这般的场面在东苑上演了数次,有时真做有时假戏,即使真来,也大多不过是楚月安龇牙咧嘴划上那么一两道,为了留个痕迹。
他心念电转,抬眼与季玉心带着担忧的视线碰上,摆摆手示意她别担心,接着以口型道:
“随你心意。”没办法,虽然楚月安一手变声术炉火纯青,但离得这么近,他方才还结结实实挨了鞭子,万一一开口没把握住不是要当场掉马?还是交给玉心吧。
于是季玉心咬咬牙,将手上鞭子一丢,虽顾少室在外看不见车内情况,她还是抱起双臂,做足了气势:
“丞相这是来英雄救美了?不过可惜……”
“他的命都是我的,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,又与丞相何干?”
她顿了顿,目光越过车帘望向顾少室:
“倒是我想问,丞相为何出现在此处?”
顾少室静静盯着马车车窗映照出来的浅浅倒影,半晌,才不咸不淡答:
“我来要人。”
车内的楚月安和季玉心俱是一愣。
这会不会太顺利了点?
季玉心显然有些犹豫,又将目光投向楚月安,楚月安自然也还是懵的,点点头又摇摇头,不知在示意她什么,便听顾少室接着道:
“怎么,难道我身为丞相,竟管不了中书省下一个小小的七品中书郎?”
“白止无故缺勤三月,派出去问访的人却都被楚小姐一应拒了回去,如今又让本相直接撞见了这么一幕——”
顾少室的声音赫然一沉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