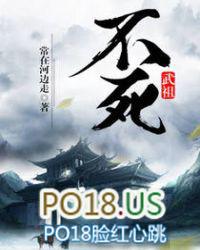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丞相总想扒我马甲 > 英雄救美(第3页)
英雄救美(第3页)
“楚小姐这是真视大衍律法如无物,还是觉得那日我放权给楚统领,而昭武少将军如今得胜归来,楚家风头无量,便无法无天了?”
……虽然时机不是很合适,但楚月安还是要说,这么说话才像顾少室嘛,前面那个说报应的像假货,真丞相才不跟你玩这些神神鬼鬼的虚妄之言。
不过话说……
这几月事情太多,当时入京时的静慈寺占地之事好像一直没有个结果?
这几个念头来得快去得也快,楚月安总算想好了对策,挣扎着扑腾了两下又猛地摔倒,膝盖在木质地板上狠狠磕碰一下,紧接着急声道:
“丞相恕罪!”
楚月安吸了两口气,他承认有演的成分,但方才那下确实疼到他了——楚月安自认不是能忍的人。
毕竟生活已经够苦,男扮女装受苦受累也至多是累个精神,他还不至于为着陆景辞多模了两下手,或是在哪个筵席上被世家公子毫不收敛的目光多盯两下而少块肉,但…
他让季玉心用点力气,却怎么也没想到,她有力气是真用啊!
不说话还好,这一提起气来楚月安当真觉得胸腔有些受压迫而产生的抽痛,坏了,不会真给他抽出内伤来了吧?
楚月安嘶声:“……丞相若罚,便依大衍律法,罚臣玩忽职守、革职踢出中书省便是……”他咳了两声,开口时声音又轻一度:
“小姐不过是在与臣玩闹,不至于触动律法,还请……”楚月安喉咙梗了一下,心觉有些羞耻,闭了闭眼,这才续道:
“还请大人高抬贵手。”
空气一时安静了。
听“白止”说完这么一席话,“楚月安”抱起双臂冷哼一声,做出一番不屑至极又强撑姿态的模样来:
“行啊,有本事你就跟他走,反正他都把自己的腰牌给你了,你们私下里有什么勾当,当我不知道吗?”
只听一声脆响,似是某种玉质物品受力磕碰,紧接是“楚月安”的冷声:“楚家不养叛徒,滚吧。”
顾少室猜是楚月安将那枚腰牌丢到了白止怀里,果不其然,下一刻,白止起身,车窗上总算出现他的身影,便见他垂首朝站立的女子一礼,低声应了句:“是。”
一只清癯苍白的手伸出,借力在门前撑了半刻,适才勉力掀开那道遮蔽一切的帘子:
“微臣见过丞——”
“不必。”顾少室硬声打断,眉头却狠狠皱了起来:
白止一张脸全无血色,一头乌发横七竖八披散肩头,左肩、手臂,乃至胸前、腰侧,无不洇染出鲜红血迹,看上去弱不禁风,一吹就倒。
可偏生,即便如此,白止见他,明明眼里的难堪和自嘲已掩饰不住,仍朝他挤出个苍白的笑,一手按住车帘,一手止住方冬欲扶他的手,而身子微微侧着,将车内的情形挡得严严实实,似是不愿他迁怒造成这一切的那位始作俑者。
顾少室心头一阵无名火起。
他猛地挥开松竹欲上前搀扶白止的手,自己上前半步,身体微微前倾,右手并左手托住楚月安手臂将人带下了地面。
楚月安猝然睁大双眸:“……大人?”
顾少室入手才发觉他身上衣物单薄非常,便是那件外衣,也不过是这严严冬日里、达官显贵们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中衣的厚度,甚至还不如,更何况鞭风何其犀利,外衣上遍处碎痕,甚至有几缕布条垂落,看上去好不狼狈。
“披着。”顾少室神色不虞,并未与他多言,只是一手捏着他瘦削手腕,一手将自己身上大衣松下,紧接着披上楚月安双肩,末了还在他脖前系紧了系带。
楚月安身体僵着任他动作,心里却是一阵莫名不适。
无他,因为这件大衣,正好是那日落水后顾少室救他上来给他披的。
后来他差使林彻送回了丞相府,现在想来,应该是他还在病中那段时日的事了,却不想现在这衣服又披回了他身上。
顾少室对他内心所想一无所知,给他穿好衣服后仍未松手,一个眼刀止住方秋要上来替他的动作,抬眼看向马车:
“楚小姐自便,告辞。”紧接着一手揽住楚月安肩头,将人带着往回走,徒留松竹“欸”一声,接着这才反应过来,回头匆匆忙忙跟上两人脚步,不忘边走边打量楚月安身上伤势,嘀咕一句:
“没想到楚小姐看上去冰清玉洁,私下里玩得这么花……”
楚月安本就跪地双腿发软,此时被顾少室拽着走地吃力,落后半步,恰将松竹这句听了个全,西风一吹,当即一口血吐出,两眼一黑,昏死过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