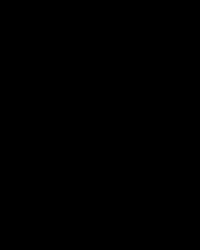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龙傲天的金手指是我前任 > 160170(第20页)
160170(第20页)
他很清楚曲砚浓绝不是什么宽和耐性的人。
“你和曲砚浓怎么说?”他勉强按捺住焦躁,问卫朝荣。
曲砚浓仰头望着冥渊。
“我有一件事不明白,”她语气疏淡,像浩荡长风入袖,缥缈不定,“为了一个结束山海断流的可能,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,值得吗?”
季颂危也不明白她这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,“难得还能不值得?”
曲砚浓自己还不是奋力补了上百年虚空裂缝,最后才立下青穹屏障的?那些困守冥渊外,无休无止补天的时光,难道不也耗尽了她的心力?
她自己也为守护五域兢兢业业,怎么现在却来问他值不值得?
“你以为我是在虚言骗人吗?”季颂危只能想到这个可能,并因此怒不可遏,瞪着眼前烈火,“你告诉曲砚浓,这世上不是只有她心怀天下。我补过的虚空裂缝难道就少了?我做这一切,当然都是为了五域,我为了五域铤而走险应对道心劫,为了五域打碎仙骨修魔,甚至为了五域不惜身死,没有人比我更想拯救这方天地!”
曲砚浓心绪平静。
“我倒不是想说这个。”经过卫朝荣转述的话干巴巴的,没有一点情绪,但她能够推测出季颂危的语气,却又不太在乎,“我只是不明白,五域兴亡也谈不上是某个人的责任,季颂危就一定要在生前解决它吗?”
她就不是这样。
曲砚浓也为五域付出了许多,但她并没觉得自己非得解决山海断流的问题,有一分力就出一分力,倘若无能为力,那只能对五域说一声抱歉了。
她能付出寿元许下誓约,也能在誓约将尽之前和卫朝荣一起遁入虚空,但往后的五域会如何,她就一点也不关心了。
她死后纵有洪水滔天,也已与她无关。
可季颂危就不是这样的人。
他是极少数能让曲砚浓感到太执迷的人,无论是他对道心劫的态度,还是对山海断流的态度,都太过执迷了。
季颂危这人,大约是不信人力有穷时的。
不信,更不愿承认。
“她觉得我是骗她的吗?”季颂危却好像怒意更盛了,他几乎难以克制,“我做这一切,难道对我有什么好处吗?沉沦于道心劫,难道是我想要的结果吗?在这五域当个魔修有什么好处吗?这个熔炉窃取的力量难道是好掌握的吗?每一次,每一次我都要在这熔炉里死去活来一回,难道我是为了我自己吗?”
卫朝荣漠然地截取了其中几个有用的字句转达给曲砚浓,“他说他没骗你,他做的一切都没好处,不是为了他自己。”
其余的牢骚,他都懒得转达。
——其实就连那两三句,卫朝荣都嫌多余。
冥渊的银辉落在起伏的幽沉海水上,既明亮,又更显暗淡。
曲砚浓盯着海水下的珊瑚枝。
“你就跟他说,我相信他确实想过对五域负责。”她说。
她确实相信季颂危曾经心里有五域。
曾经一起在虚空裂缝前并肩作战的人,也曾为五域拼尽全力。
但相信,又有什么用呢?
她曾经什么也不相信,不信承诺、真情、责任,也不信任何人,只因她那时将这些美好的东西看得太纯、太正、太高、太罕有。
而她现在终于相信了这些东西,却也将它们打落神坛。
责任、真心、承诺是存在的,但它们的存在也不代表什么,它们会变,会消失,会背叛。
即使这一刻季颂危有一刻粉身碎骨甘愿救世的真诚之心,对她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。
——她本也只剩下四十年光景。
有玄金索束缚,卫朝荣多半不会在这四十年内失控,他们必然能安静相伴四十年,也只能安静相伴四十年,那她何必和季颂危合作呢?
真心不真心,本也没那么重要。
曲砚浓想到这里,心里忽而一动。
然而等她追溯这莫名的灵光时,却又一时追溯不到来处了。
她莫名怅然。
神塑化身开口,“他又说了一通苦衷、一心为五域、绝不是为了自己的话,全是重复的牢骚。”
曲砚浓回过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