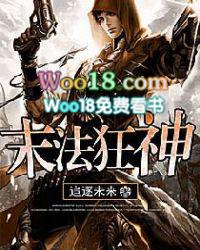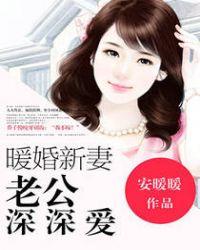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风水大师丘延翰 > 第2章 哑儿五年(第2页)
第2章 哑儿五年(第2页)
陈抟却不管这些,画完了,就把石子往兜里一揣,又坐回青石板上,盯着河面看——好像刚才那幅“神作”,不是他画的一样。
陈抟妈心里又惊又喜,捡起地上的菜,拉着陈抟往家走。路过的人都跟她道喜,她笑着应着,心里却打鼓:俺娃到底是啥来头?咋懂这么多?
这天晚上,月亮挂在涡水的上空,银闪闪的光洒在院子里。
陈抟妈哄陈抟睡觉,给他盖好小被子,刚要吹灯,陈抟突然坐了起来。
他指着窗外的河面,小手在空中比划——一会儿画个圈,一会儿指一指月亮,嘴里还“咿呀咿呀”地喊,像是在跟谁说话,又像是在呼唤啥东西。
“娃,你咋了?”陈抟妈赶紧凑过去,把灯举高了点,“你想喊啥?是想喊爹,还是想喊娘?”
陈抟不回答,只是把小手伸到灯底下。
就在这时,陈抟妈眼睛瞪圆了——
陈抟的指尖,又亮起了那丝白光!比白天在河边时亮了点,像极了揉碎的月光,沾在指尖上,轻轻晃着。那光不烫,也不刺眼,就这么温温柔柔地亮着,映得陈抟的小指甲盖都泛着粉。
“娃!你指尖咋会亮?”陈抟妈伸手想碰,陈抟却把手缩了回去,又指了指河面,“咿呀”了两声,好像在说“你看那边”。
陈抟妈顺着他指的方向看——河面静悄悄的,只有月亮的影子在晃,啥都没有。她再回头问陈抟,陈抟却躺了下去,闭上眼睛,好像累了,只留指尖那点白光,慢慢暗了下去,最后没了踪影。
这一夜,陈抟妈没睡好。
她总在想:娃指尖的光是啥?他指河面,是看见啥了?他到底想喊啥?
更让她心跳的,还在后头——
陈抟有个习惯:每天睡前,都要把那片龟甲残片放在枕头边。
那残片还是他三岁时攥在手里的,这些年从没离过身。陈抟妈想帮他收起来,他还不乐意,非得自己拿着,睡觉时就摆在枕头边,像个宝贝。
这天半夜,陈抟妈被尿憋醒,轻手轻脚起来,想看看陈抟盖好没。
月光刚好从窗户纸的破洞里钻进来,斜斜地洒在陈抟的枕头上——那片龟甲残片,正躺在月光里,泛着温润的光!
不是平时的淡褐色,是带着点银的光,像蒙了层薄霜。更奇的是,残片上原本模糊的纹路,竟慢慢显了出来!
那纹路细细的,弯弯曲曲,一会儿像小虫子在爬,一会儿像星星排着队,还有几个小小的“圈”,跟陈抟白天画的河湾有点像。纹路在月光里轻轻闪,好像活过来了一样,在残片上慢慢动。
陈抟妈吓得捂住嘴,不敢出声——这残片咋会发光?这纹路是啥?
她站在床边,看了好一会儿,腿都麻了。想伸手摸摸,又怕吵醒陈抟,只能眼睁睁看着那纹路在残片上晃。
首到天边泛起鱼肚白,月光慢慢淡了,残片上的光才暗下去,纹路也跟着不见了,又变回了那片普通的淡褐色残片,安安静静躺在枕头上。
陈抟妈揉了揉眼睛,再看——残片还是老样子,啥光都没有,啥纹路都看不见。
“难道是我眼花了?”她嘀咕着,心里却发慌,“还是这残片真有啥古怪?”
打这天起,陈抟妈的心思就没闲过。
她天天观察陈抟,越看越觉得自家娃不一般。
比如早上晒衣服,陈抟指着晒在竹竿上的被子,“咿呀”两声。陈抟妈纳闷,刚想问问,天上就飘来乌云,没一会儿就下起雨来——她赶紧收衣服,还好没淋湿。
比如中午喂鸡,陈抟指着鸡窝,“咿呀”两声。陈抟妈过去一看,鸡窝里卧着个热乎乎的鸡蛋,还是双黄的!
比如狗蛋他爹去河里打鱼,临走前问陈抟:“哑儿,今儿个去东边下网能打着鱼不?”陈抟摇摇头,指了指西边。狗蛋他爹半信半疑去了西边,傍晚回来时,挑着满满一筐鱼,笑得合不拢嘴:“哑儿真神!东边今儿个没鱼,西边全是大鲫鱼!”
村里的人也越来越信陈抟“通神”。谁家丢了鸡,谁家找不着锄头,都来问陈抟。陈抟要么指个方向,要么点点头摇摇头,还真能帮上忙。
可陈抟妈却越来越愁:娃能通这么多事,咋就不能开口说话呢?那指尖的白光、残片的纹路,到底是啥意思?
有天傍晚,王婶来串门,手里拿着块花布,想给陈抟做件新衣裳。她坐在炕边,看着陈抟玩残片,笑着说:“陈婶子,你说陈抟是不是等啥时候?比如等那残片发光,他就会说话了?”
陈抟妈叹了口气:“谁知道呢?老道士说红尘劫,我看这‘不说话’,就是咱娃的劫。”
正说着,陈抟突然举起残片,对着窗外的月亮晃了晃。
王婶和陈抟妈都抬头看——月亮刚升起来,圆溜溜的,银光照在残片上,残片又开始泛光!比上次半夜看到的还亮,纹路也更清晰了,像极了老秀才家那本旧书里画的“圈圈叉叉”(后来陈抟妈才知道那是八卦)。
陈抟指尖的白光也亮了,跟残片的光映在一起,小小的手举着残片,对着月亮“咿呀”喊,好像在跟月亮说话。
王婶吓得赶紧站起来:“我的娘!这、这是要成仙啊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