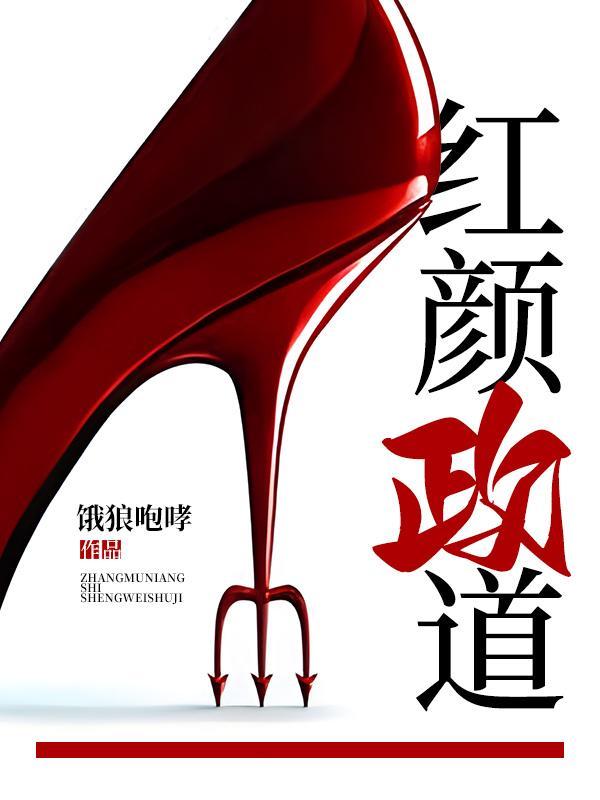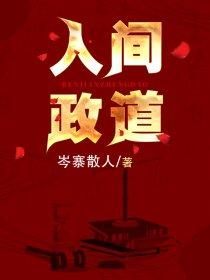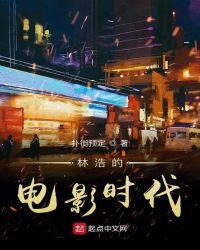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网>屠户子考状元 > 第11章 晨光备学 书包里的期许(第1页)
第11章 晨光备学 书包里的期许(第1页)
十一月初一的天,亮得比往常更迟些。鸡叫第二遍时,柳氏就己经醒了,摸黑从床底下拖出那个藏了许久的木匣——里面放着给陈砚缝书包的蓝布,是大姐出嫁时剩下的料子,颜色虽不算鲜亮,却细密柔软,是家里最好的布。她点上油灯,昏黄的光线下,布面上的暗纹隐约可见,她指尖着布料,想起前几天熬夜缝书包的模样,嘴角忍不住弯了弯。
那几天,柳氏几乎每晚都缝到半夜。白天要忙着做饭、喂猪、打理菜园,只有等夜里家人都睡熟了,她才能坐在油灯下,就着微弱的光穿针引线。书包的边角要缝云纹,她特意去村里李秀才家,借了本画着云纹的旧书,对着上面的图案,一针一线地描;里层要垫软布,她把自己穿了三年的旧棉袄拆了,取出里面的棉絮,裹上细布,缝在书包内侧——怕书本边角硌着陈砚的手,也怕走路时书本晃得太厉害。
“娘,您又起这么早。”陈砚揉着眼睛走出房间,身上穿着王氏新缝的粗布小褂,领口和袖口都缝了细细的滚边,是王氏特意学的新样式。他走到柳氏身边,看着桌上的青布书包,伸手轻轻摸了摸——布料柔软,针脚细密,云纹在晨光下透着精致,里层的软布更是暖乎乎的,贴着手心舒服得很。
“这书包缝得真好,娘。”陈砚的声音里满是欢喜,他把书包抱在怀里,像抱着个宝贝。
柳氏笑着拍了拍他的头,伸手帮他理了理衣领:“喜欢就好。到了学堂,可别把书包弄脏了,里面还放了两张油纸,下雨时把书本包好,别弄湿了。”她说着,又开始反复叮嘱,“跟先生说话要客气,别跟同窗吵架;先生讲课要是听不懂,就课后问,别不好意思;中午饿了就吃你大哥给你塞的麦饼,别省着,下午还要上课呢……”
她的话絮絮叨叨的,像春日里的细雨,落在陈砚心上,暖融融的。陈砚知道,娘是怕他在学堂受委屈,怕他跟不上功课,这些叮嘱里,全是满满的牵挂。他认真地点头,把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:“娘,我知道了,您放心,我一定好好学,不惹事。”
这时,陈武扛着锄头从外面回来——他一大早去地里看了圈白菜,怕夜里下霜冻坏了。看到陈砚抱着书包,他放下锄头,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,塞到陈砚手里:“三郎,这是娘昨天晚上特意给你做的麦饼,里面夹了点猪油和盐,比平时的好吃,饿了就吃,别省着。”
陈砚接过布包,能摸到里面两个圆圆的麦饼,还带着点余温。他知道,家里的猪油是上个月杀猪时炼的,平时都舍不得吃,娘却特意用在麦饼里,就是想让他在学堂能吃好点。他捏了捏布包,抬头对陈武笑:“谢谢大哥,我会吃的。”
陈老实也从屋里走了出来,手里拿着陈砚的《千字文》和《三字经》,用细麻绳捆着,还在外面包了层粗布。他把书递给陈砚:“把书放进书包里,别弄丢了。到了学堂,跟先生问声好,好好听课,爹下午来接你。”
“嗯!”陈砚用力点头,小心翼翼地把书放进书包里,又把麦饼放在旁边,拉上书包的系带——系带也是柳氏用蓝布编的,还打了个漂亮的结。他背上书包,书包的重量刚刚好,贴在背上很舒服,一点都不沉。
一家人送陈砚到门口,柳氏又叮嘱了几句“路上小心”“别跟人打架”,陈武则拍了拍他的肩膀,让他“别怕,有大哥在”。陈砚背着书包,跟在陈老实身后,一步三回头地朝着学堂走去。晨光洒在他身上,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,书包上的云纹在阳光下闪着淡淡的光,像藏着全家人的期许,陪着他走向新的路。
走在路上,陈老实怕陈砚走得累,特意放慢了脚步,还跟他说学堂里的事:“周先生是个好先生,你好好听他的话,肯定能学好。要是有同窗欺负你,别忍着,回来跟爹说,爹去帮你说理。”
陈砚笑着点头,心里却暗下决心:自己不能总靠爹和大哥,到了学堂,要自己照顾好自己,还要好好读书,不辜负家人的期望。他摸了摸书包里的书,又摸了摸麦饼,感觉心里满满的,一点都不害怕了。